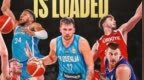作者:Cynthia Wu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Off Screen》(1999年4月刊)
1998年5月,在张艺谋的新电影开始拍摄的十天后,我带着好奇心,坐着一辆桑塔纳来到张家口——一个离北京约四小时车程的城市,去采访这位著名导演。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想要采访到张艺谋太难了。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北京,而不是在蒙特利尔电影节,我都很难找到他,他经常受到狗仔队的围追堵截,因此,记者必须先与他的制片人胡晓峰联系。然后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采访者一起被列入一个长长的等待名单。最后在剧组的面包车上等待空位,这辆车每周只开往剧组一次,前往拍摄地点张家口。
除了采访张艺谋之外,我还有机会与他长期合作美术指导曹久平和摄影师、他曾经的同学侯咏交谈。
当我到剧组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剧组成员穿着写有「张艺谋剧组」的T恤,上面印有从《红高粱》到《一个都不能少》,甚至歌剧《图兰朵》和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片名字样。

我和其他记者被安排在张家口最好的一家宾馆。就在我打开行李箱时,一个小女孩跳到我面前,问道:「姐姐,你也是剧组的吗?」她好奇而天真地看着我。
制片人胡晓峰向我介绍了她:「这位是魏敏芝,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后来我了解到,魏敏芝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学生是张艺谋从数千名当地女学生中挑选出来的。除了她之外,其他十位主演都是从一万多名试镜者中挑选出来的非职业演员。我觉得年仅十三岁的魏敏芝无论怎么说都还是个孩子。

「我们希望她看起来真实而简单。这个女孩的简单性格符合电影中的角色。」
制片人进一步解释说,「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尽力保持她在生活里的样子。我们不让她看电视,因为我们认为电视会使她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多。而最坏的情况是,一些不太健康的信息可能使她迅速成熟。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们聘请了一位学校里的教师来陪伴她,帮助她学习。在电影中,她是整个学校的老师,有时还得管比她大的学生。」

午饭时间,张艺谋出现在食堂,穿着红色T恤和黑色牛仔裤。张的饭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肉末、土豆片、馒头和鸡蛋汤。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普通的情况下遇到传说中的张艺谋。
我惊讶地看到他还保持着如此简单的生活方式,而他那些杰出的作品却席卷了国际上那么多电影节的奖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电影史留下印迹的杰作。而且张艺谋从未抱怨过拍摄地的恶劣条件。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辍学问题。故事的主角是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她为了让学生能留在学校接受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包括寻找一名在城市中失踪的学生,以便她能够履行影片中对学生的承诺:「一个都不能少。」

剧组第一晚的场景在离我们酒店约40分钟车程的一个老式电视台里拍摄。故事中的魏敏芝在发现她的学生张惠科失踪后,来到这里寻求帮助。电视台的两位当地女主播播报了她的消息。张艺谋在房间外的监视器前指挥拍摄,看起来严肃、专注。他一会儿说「开始!」 ,一会儿说「停!」 ,声音低沉但坚定有力。
休息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决定拍一部以孩子为中心的电影?」他回答说:「电影中的魏敏芝第一次独立、成功地完成了一件事。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是我拍的最具挑战性的电影之一。但它肯定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
他的助手补充说,为这部作品带来更多力量的是,这个故事讲述了农村儿童在追求知识方面的非凡努力。因此,这部电影向整个社会提出了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拍摄结束后,剧组向该村捐赠了一所全新的学校——水泉小学。

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评论家认为张艺谋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帮助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进程。在他早期的电影中,张艺谋尝试了不同的风格。
《红高粱》以民谣式的叙事而著称;而《秋菊打官司》则作为第一部 「中国电影中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 」脱颖而出。《一个都不能少》与《秋菊打官司》一样,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纪录片式风格;但是,正如张艺谋所解释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也非常不同。《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启用非职业演员的电影。

我在拍摄的间隙采访了张艺谋。
问:你怎么看待《一个都不能少》中的现实主义?在这部电影中你第一次大量地使用了没有表演经验的演员,你为什么这么做?
张艺谋:当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用现实主义的风格来拍这部影片,剧组对此讨论了很多,我们最终决定使用这种「生活式纪录片」的风格来拍这个故事。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剧情片,不是纯粹的纪录片。我认为,即便是纪录片也带有某种主观的视角。
当某个事件发生时,除非你在现场用摄影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否则很难说这是一部具有客观性的、纯粹的纪录片。它就像某种对社会的观察和采访,我们在这部电影中谈论的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影片的故事也是对过去的事情的总结,我们在片中呈现的是自己的主观视点。

这个片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你刚刚说的使用非职业演员。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无论专业与否,演员们演的都是和他们生活很远的事。戏剧冲突是编出来的,它只发生在故事里。
尽管我也使用了与角色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演员,但他们做的动作与他们自己过去做的不完全一样。他们做的只是模仿,或者重演某些和过去相似的情节。电影中的学校老师、校长、电视台老板,甚至门卫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演的就是自己,其中一些人已经工作二十多年了。
问:你是怎么在剧情片和纪录风格之间保持平衡的呢?
张艺谋:剧情片在制作层面确实和纪录片不同。它不那么客观,因为导演用电影作为媒介表达了一种主观的观点。我希望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一部纪录片,看起来很真实。「真实」指的是一种现实的风格。在拍一部剧情片的同时,我们也用纪录片的风格来反映现实。什么是剧情片?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反映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现实主义风格」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去拍一部纪录片。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当我拍电影时,它又变成了主观的,里面有我自己对小说的解释,我组织场景的方式。导演的反映不是客观的,因为我们是从感兴趣的角度出发,表达自己的观点。

问:我注意到,你总是特别关注画面壮观的视觉效果,例如《红高粱》。你以前是一个摄影师,后来转去做了导演。在视觉上,你对《一个都不能少》有什么想法?
张艺谋:我之前的确做的是摄影,所以对我来说,壮观的画面不仅震撼,还很重要。我总是对画面很敏感,这是我的一贯风格。在《一个都不能少》中,我们试图通过画面向观众传递真实的信息,和《秋菊打官司》的拍法一样,我们把摄影机藏了起来,镜头拍的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人们进进出出,不知道他们正在被摄影机「观察」。
另一方面我还很关注画面的质量,我发现用这种方法拍出来的影像很漂亮,即便看上去不完美,但它依然是美丽的。这是我们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复制或者创造出来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追求的效果,我们会开始习惯对影片中的细节进行调整。当然我们肯定达不到像生活那么真实、那么自然的感觉,但我和我的团队都相信这会是一部好电影,观众会喜欢它的。
问:你怎么看待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
张艺谋:我认为,流行文化应该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一种目的。一个人必须使用某种媒介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西方的电影有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目的,为了迎合市场。他们的电影是为了追求时尚,这样就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全世界的电影业都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如果只是让一部片子变得受欢迎,那是不够的,我必须要表达我想说的东西。
我可能不会拍一部所谓的流行作品。我想通过电影对观众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说,流行文化是一种媒介,一个过程,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你的想法,我当然也希望我的作品被观众接受。这很重要。
但这也不代表艺术家只去表达想说的东西,而忽略了观众。我觉得我们也是凡夫俗子,并没有比谁高明。受大众欢迎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它是一种风格,而且只有当我们能够充分表达观点,并把流行文化真正作为一种工具和媒介时,它才能在电影中发挥作用。

问:你的电影得了不少国际大奖,这也只是巧合吗?你怎么看待西方电影界对你的评论?
张艺谋: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来评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过,即便电影节的评审团喜欢一部电影,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部好电影,它只反映了评审团的喜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评审团可能也许只是对他们从未见过的、真实的、在他们社会中很难找到的东西感到好奇。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我们观看他们,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问:我把你的《红高粱》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做了一个对比,我发现《红高粱》中更加强调象征意义和文化内容。你是否特别关注电影的象征内容,并有意通过电影来传达这种信息?
张艺谋:是的。正如我所说,一部作品应该有独特的想法。我认为许多好莱坞电影的世界观是单一的,他们不谋求内容的突破,不强调象征性,而是用娱乐元素来吸引观众,比如煽情的手段和高科技。
这些电影的成本往往都很高,有些电影拍的不错,有爱情戏和动作戏,但就艺术价值和象征性而言,其中的很多电影都乏善可陈。这些影片只是简单地给观众划出了道德的界限,比如凸显善恶的区别,观众早在高中就接受过这类教育了。
我认为电影应该反映的内容远不止如此,它应该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去拍不同的生活,最终回归人本身。这更符合电影的发展,更利于更有深度的内容的呈现。当然,还是那句话,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同的。